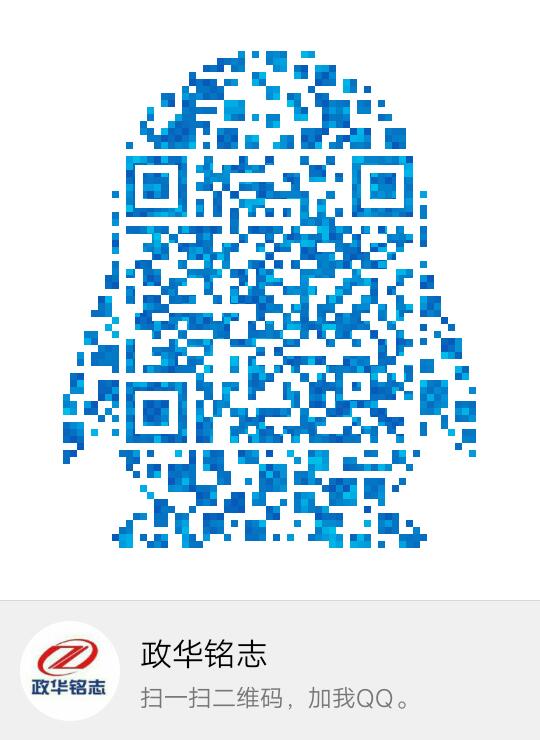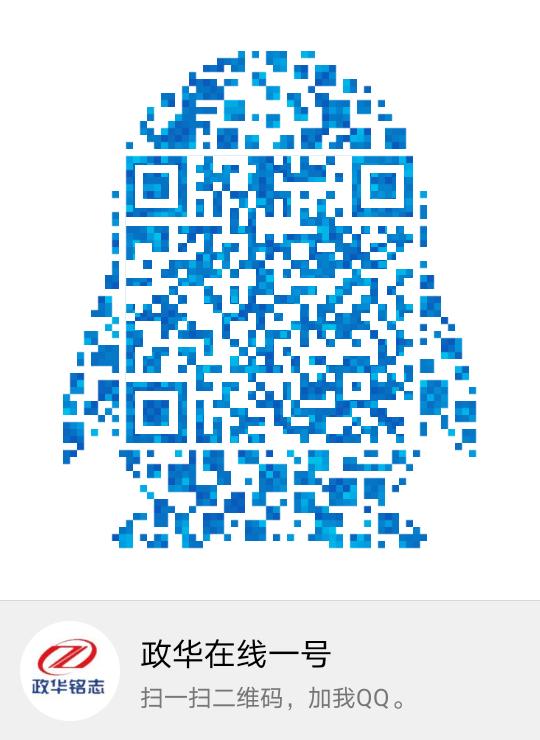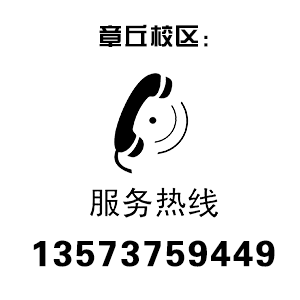互毆與防衛(wèi)到底怎么區(qū)分?
互毆與防衛(wèi)關系之檢討
——以類型化的實體與程序規(guī)則構(gòu)建為中心
內(nèi)容摘要:司法實踐動輒將故意傷害案件作為互毆而否定正當防衛(wèi)。傳統(tǒng)理論以傷害故意、報復動機、事先有無斗毆意圖等作為認定互毆的標準,這種“意圖中心論”的立場不具有可操作性,無法解決互毆的泛化問題。應當從正當防衛(wèi)的優(yōu)越利益原理出發(fā),將互毆分為真正的互毆和不真正的互毆。真正的互毆應限定為雙方事先約定相互攻擊行為(簡稱“約架”),只有這種意義上的互毆與防衛(wèi)才是互斥關系,通過互毆認定時點的前置,既能防止互毆的泛化,又具有可操作性;不真正的互毆并非一概排斥防衛(wèi),回歸到一般的故意傷害、防衛(wèi)意圖、預期侵害、自招侵害等框架下進行類型化的解決,在此基礎上構(gòu)建類型化的認定規(guī)則。與實體認定規(guī)則相適應,涉互毆案件的證明對象進行客觀化和前置化的改造。
關鍵詞:正當防衛(wèi) 互毆 約架 預期侵害 挑撥防衛(wèi)
引言
互毆與防衛(wèi)是我國刑法理論和實踐中最為復雜和混亂的問題之一。司法實踐動輒將打架、傷害行為認定為互毆,導致互毆的泛化;理論界固守“互毆與防衛(wèi)是互斥關系”的觀念,缺乏對互毆的類型化、精細化的研究。[①]一直以來,學界對于互毆與防衛(wèi)關系的觀點出奇得一致:互毆的雙方都屬于不法行為,因而都無權(quán)主張正當防衛(wèi),只有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存在正當防衛(wèi):一方停止侵害,另一方繼續(xù)侵害;輕微互毆中一方突然使用殺傷力很強的工具等。[②]這種粗放式的研究加劇了互毆的泛化。刑法界在反思正當防衛(wèi)條款“僵尸化”成因的時候,似乎遺漏了“互毆”這一重要因素。急需重新審視互毆與防衛(wèi)的關系,對互毆中的正當防衛(wèi)問題進行類型化的分析,并從實體和證據(jù)兩個方面提出類型化的認定規(guī)則,按照案件的類別得出不同的解決方案。
一、互毆中正當防衛(wèi)司法亂象的梳理
對裁判文書網(wǎng)上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涉及互毆的故意傷害案一審刑事判決書進行統(tǒng)計分析,此類案件共計14640件,其中裁判理由涉及正當防衛(wèi)的僅930件,占案件總數(shù)的6.3%。在這930件涉及正當防衛(wèi)的案件中,涉及無罪判決的共計8件,其中以正當防衛(wèi)為由判處無罪的僅1件;因證據(jù)不足全案判無罪的2件;因情節(jié)顯著輕微判處無罪的1件;其余4件均為共同犯罪中其中一名被告人因證據(jù)不足而判無罪。上述數(shù)據(jù)表明,案件一旦涉及互毆,認定正當防衛(wèi)的幾率不到萬分之一。不認定正當防衛(wèi)的理由有的表述為“互毆”,有的表述為“均有傷害對方的故意”,有的表述為“不符合正當防衛(wèi)的條件”等,實質(zhì)的理由都與互毆有關。實踐中,以互毆為由否定正當防衛(wèi)的情形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類型:
(一)打架就是互毆
司法實踐對故意傷害案件習慣于不論起因和是非對錯,只要打架就認定為互毆。司法人員關注的是誰死、傷了。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慣性思維——“打架就是互毆”,而互毆中“誰死傷,誰有理”。司法人員很少會仔細審查打架起因中是非對錯的證據(jù),司法文書中也很少表述這方面的內(nèi)容。故意傷害案的裁判文書對事實的經(jīng)典表述是:“因瑣事發(fā)生爭吵……互毆……”。
(二)還手就是互毆
故意傷害案的基本形態(tài)表現(xiàn)為一方毆打另一方,另一方還手,形成兩人對打局面,司法實踐往往會將其界定為“互毆”,導致“只要還手就是互毆”,進而否定正當防衛(wèi)。比如下面這個案例:
【案例1:羅某故意傷害案】被告人羅某在某工地項目部勸解被害人劉某等人撕扯工地安全員曹某時,與被害人劉某發(fā)生爭執(zhí),被害人劉某持木棍毆打了被告人羅某后,被告人羅某在劉某的鼻部毆打幾拳,致使被害人劉某鼻部受傷流血的事實(雙側(cè)鼻骨骨折屬輕傷二級)。被告人羅某辯稱劉某先動手打他,然后他才打的劉某,不是故意傷害。判決認為被告人羅某與被害人互毆中,具有傷害故意,以犯故意傷害罪判處管制六個月。[③]
此案中,羅某被對方持木棍毆打,出拳反擊應屬防衛(wèi)。不能苛求被告人“打不還手”,也不能因被告人還手就認定為互毆。
(三)有傷害意圖、報復等動機就是互毆
司法實踐一般采取防衛(wèi)意圖必要說,并認為防衛(wèi)意圖與傷害意圖(故意)是互斥的。但是防衛(wèi)意圖和傷害意圖作為被告人的主觀想法,相互交織是常態(tài),難以從規(guī)范的角度進行區(qū)分,也難以從證據(jù)上證明,導致實踐中動輒以行為人有傷害意圖(故意)為由認定為互毆,進而否定正當防衛(wèi)。比如下面這個案例:
【案例2熊某某故意傷害案】被害人王某、銀某、楊某等人酒后在街上閑逛,被告人熊某某開車路過,銀某無故拍打熊某某的車門,雙方發(fā)生口角。銀某用手拉住熊某某的衣領,并將熊某某嘴里正在抽的煙頭按在熊某某嘴角上,并打熊某某臉部,楊某等人打熊某某頭部。熊某某打開隨身攜帶的跳刀下車,雙方互毆(銀某一方有人持鋼管和電焊坨),熊某某用手中的刀亂刺,致使王某死亡、銀某等3人受傷。判決以被告人熊某某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檢察機關認為系防衛(wèi)過當,判決認為被告人主觀目的是“對方如果打自己就亂捅”,說明有傷害故意,是互毆,不是防衛(wèi)。[④]
此案中,銀某等四人酒后滋事,抓衣領、用煙頭燙、毆打面部、持械毆打,暴力步步升級,熊某某持刀反擊,判決認定為互毆而排除防衛(wèi),恐有不妥。
(四)事先有糾紛、事先準備工具就是互毆
傷害案件中事先有糾紛是常態(tài),事先準備工具一般意味著行為人具有預期侵害,可能會影響防衛(wèi)的認定,但不能一概排除防衛(wèi)。比如下面這個案例:
【案例3卜某某故意傷害案】被告人卜某某因瑣事與其親戚王某乙在某購物廣場二樓發(fā)生口角,進而廝打,被人勸開。后卜某某回到一樓其經(jīng)營的建材店內(nèi)拿出一把木把單刃尖刀。卜某某稱“王某乙在二樓仍然喊著要弄死我,他若再打,我就拿刀捅他幾刀,讓他走不成了他就不能打我了。”王某乙持木棍到一樓追打卜某某,并揚言要弄死卜某某。卜某某繞著汽車躲避逃跑,王某乙用木棍追打,后卜某某持刀刺中王某乙背、臀、腿部(后王某乙死亡)。判決認為:卜某某供稱在超市二樓打架時沒有拿東西吃了虧,因而氣惱,故準備了刀具,若王某乙再次毆打,就捅他幾刀,故其主觀上有傷害的故意,不構(gòu)成正當防衛(wèi)。以被告人卜某某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三年。[⑤]
本案中,被告人為了防止對方下樓繼續(xù)毆打而準備工具防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被對方持木棍追打的情況下反擊,并不因此前準備工具而喪失防衛(wèi)權(quán)。
(五)先動手就不能防衛(wèi)
一般情況下,一方先動手,另一方可進行防衛(wèi),先動手一方不得主張防衛(wèi),但并非任何情況下先動手一方都不能防衛(wèi)。實踐中往往片面地認為先動手就不能防衛(wèi)。比如下面這個案例:
【案例4李某故意傷害案】被告人李某及老鄉(xiāng)肖某等在某棋牌室內(nèi),與被害人彭某、郭某等多人發(fā)生爭執(zhí),并打架(李某等人先動手)。后彭某、郭某等人持棍子毆打被告人李某等人,被告人李某、肖某等人逃跑,李某在逃跑中落單,被彭某、郭某追上。彭某按住李某,郭某用木凳砸,李某則持匕首將彭、郭二人捅傷(彭某重傷、郭某輕微傷)。判決認為,被告人李某等人毆打彭某在先,彭某等人因此才追打李某,最終發(fā)生李某持匕首捅刺,雙方均有責任,被告人李某行為不具備防衛(wèi)性質(zhì),以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⑥]
此案中,盡管李某先動手,但后逃跑被追上,并被兩人圍毆的情況下進行反擊,以李某在前一階段先動手為由認定其自始喪失防衛(wèi)權(quán),值得商榷。
(六)防衛(wèi)前要先躲避
正當防衛(wèi)與緊急避險不同,防衛(wèi)人原則上沒有退避義務,但實踐往往強加退避義務。比如下面這個案例:
【案例5聶某某故意傷害案】被告人聶某某駕車在某理發(fā)店門口停車時,車門被隔壁飾品店主習某9安置的地鎖刮擦,聶某某踹了幾下地鎖后,即到理發(fā)店理發(fā)。習某9遂電話告知其兄習某5,習某5到場后在理發(fā)店外叫罵,踢聶某某的轎車。聶某某見狀沖出理發(fā)店,跟自己的同鄉(xiāng)與習某5發(fā)生沖突、互毆,后雙方被勸離,聶某某駕車離開。習某5的堂兄習某6等人聞訊后持鐵鍬等先后趕到現(xiàn)場,遇返回現(xiàn)場的聶某某,遂與習某5一起對聶某某追打。聶某某逃跑過程中撿起木棒,與身后持手鋸的習某5對打,擊中習某5頭部,習某5當即倒地(后死亡)。聶某某丟掉木棒繼續(xù)逃跑,習某6等人持鐵鍬等繼續(xù)圍打,聶某某受傷后鉆入皮卡車下躲藏。判決認為,被告人聶某某被習某5等人持械追打時不是采取緊急避險的方式,而是在自身并沒有受到傷害時,撿起木棒以暴制暴與習某5對打,擊中習某5的頭部,該行為不構(gòu)成正當防衛(wèi),以聶某某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⑦]
此案中,雙方被勸離后,習某糾集多人追打(且有人持手鋸),聶某某撿起木棍反擊,應屬防衛(wèi)。判決要求聶某某只能緊急避險,這是難以接受的。
上述亂象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互毆的泛化。這種互毆的泛化與“唯結(jié)果論”相互交織,一旦一方出現(xiàn)傷亡后果,就傾向于否定另一方的正當防衛(wèi),而否定正當防衛(wèi)的最佳借口就是互毆,從而加劇了互毆與防衛(wèi)關系的混亂。要改變這些現(xiàn)狀,就需要從理論上反思,嚴格限制互毆內(nèi)涵,強化其規(guī)范屬性,構(gòu)建切實可行的類型化認定規(guī)則,避免簡單化、形式化的思維方式,去實質(zhì)地探究防衛(wèi)存在的空間和余地。
二、互毆的內(nèi)涵及其與防衛(wèi)關系之檢討
(一)傳統(tǒng)互毆內(nèi)涵的反思
什么是互毆?有人認為互毆是指斗毆雙方都有侵害對方的故意;[⑧]有人認為互毆是指參與者在其主觀上不法侵害故意的支配下,客觀上所實施的連續(xù)的互相侵害行為。[⑨]有人認為互毆必須以雙方事先存在斗毆意圖為前提,只有先產(chǎn)生斗毆意圖才能排除防衛(wèi)。[⑩]有人認為互毆是參與者在傷害故意和斗毆意圖的支配下所實施的相互傷害的行為,并認為斗毆意圖是指基于欺凌、報復、逞強斗狠、尋求刺激等動機而主動挑起斗毆或積極參與斗毆的主觀心態(tài)(即傷害故意+斗毆意圖)。[11]
上述觀點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試圖從斗毆意圖這一主觀要素來界定互毆,這種“意圖中心論”的立場是互毆泛化的重要原因,值得反思。
首先,正當防衛(wèi)中原本就存在侵害或傷害對方的故意,從侵害、傷害故意的角度根本無法區(qū)分互毆與防衛(wèi),反而會導致“只要有傷害故意就是互毆”的現(xiàn)象。前述案例2熊某某故意傷害案,盡管根據(jù)樸素正義都會覺得不認定正當防衛(wèi)是不妥的,但按照傳統(tǒng)觀點對互毆的界定來審視判決的理由,好像并無明顯漏洞。這說明傳統(tǒng)觀點對互毆的界定是有問題的。正當防衛(wèi)本來就是保護一種法益而犧牲另一種法益,故防衛(wèi)人必然有希望或放任對方法益損害后果之心態(tài)。即便在典型的正當防衛(wèi)案例中,防衛(wèi)人也會明知反擊行為會導致對方傷亡后果,甚至還帶有“教訓一下對方”的心理,至少會放任后果的發(fā)生,但這并不影響正當防衛(wèi)的成立。比如昆山于海明案,于海明搶到砍刀后多次捅刺劉某,在劉某受傷后跑向轎車時,于海明繼續(xù)追砍2刀(未砍中)。[12]如何能確定于海明多次砍向劉某時沒有傷害的故意?沒有任何傷害故意的正當防衛(wèi)在實踐中幾乎是不存在的。的。即使按照最嚴格的標準和條件來認定正當防衛(wèi),也無法排除防衛(wèi)人具有傷害的故意。“如同防衛(wèi)行為當然包含了傷害行為一樣,防衛(wèi)意思當然可能包含傷害對方的意識”。[13]防衛(wèi)意圖與傷害故意并存是常態(tài),更何況實踐中根本無法區(qū)分二者。日本曾有判例認為防衛(wèi)意思不能與傷害故意并存,但是時至今日,無論是判例還是日本理論通說,均認為防衛(wèi)意圖與故意傷害并存時可以成立正當防衛(wèi)。[14]
其次,將互毆限定為“事先產(chǎn)生斗毆意圖”不具有可操作性。該觀點的提出者陳興良教授以防衛(wèi)意思必要說為出發(fā)點,力圖限縮解釋互毆的內(nèi)涵,從防衛(wèi)意圖與斗毆意圖互斥關系的角度推導出互毆與防衛(wèi)的互斥關系。可問題是斗毆意圖與防衛(wèi)意圖如何區(qū)分?二者并存時如何處理?陳教授限縮解釋互毆的思路值得欽佩,但他提出的方案不具有可操作性,會導致“只要事先準備工具、有報復動機就是互毆”。因為實踐中會將準備工具、報復動機等解釋為事先就有斗毆意圖。比如前述案例3卜某某故意傷害案,卜某某準備刀具是屬于防止對方再次追打的防衛(wèi)意圖,還是因前一階段吃虧而產(chǎn)生的斗毆意圖呢?這是個無法說清楚的問題。陳教授將該觀點應用到其所引用的姜方平故意傷害案中,認為被告人姜方平屬于事先產(chǎn)生斗毆意圖而不成立正當防衛(wèi)。[15]這一判斷值得商榷。此案中,姜方平在得知鄭永良向其父親挑釁后前往鄭永良家,因鄭不在家而返回,在返回途中從別人家廚房順手拿了一把菜刀,到底是為了防止鄭永良追上來而防身,還是出于斗毆意圖?似乎不能絕對化。如果事先有斗毆意圖,那就應該在去鄭永良家之前準備菜刀,為何在返回途中準備呢?后來果然被鄭永良持鐵棍追打(不排除鄭永良在向姜方平父親挑釁時系挑撥防衛(wèi)),此時姜方平就喪失防衛(wèi)權(quán)而只能坐以待斃嗎?如果姜方平途中準備的不是一把菜刀,而是一根細小的樹枝,在面臨對方持鐵棍毆打要害部位時,是不是也不能防衛(wèi)?如果能防衛(wèi),那么準備菜刀就至多是防衛(wèi)過當與否的問題,而非能否防衛(wèi)的問題。可見,用“事先有斗毆意圖”這個標準來界定互毆是靠不住的。
最后,從“傷害故意+斗毆意圖”的角度重構(gòu)互毆概念的觀點基本上停留于文字游戲?qū)用妗?/span>該觀點不僅沒有跳出“意圖中心論”的窠臼,反而又加上欺凌、報復、逞強斗狠、尋求刺激等動機,這種隨意添加主觀超過要素做法,將正當防衛(wèi)進一步“道德潔癖化”。前述案例2中,被告人熊某某被毆打、被煙頭燙,任何正常人都會滿腔怒火,想要報復,但據(jù)此就能否定正當防衛(wèi)嗎?同樣,案例3中卜某某供述稱“他若再打,我就拿刀捅他幾刀”,這里確有報復成分,甚至也可以說有逞強斗狠的意圖,但是也可以理解為“你若行兇,我就要防衛(wèi)”。事實上,一個人正常的理性人,在面對不法侵害時都會有憤怒、仇恨、報復等動機,但這些動機并不影響防衛(wèi)的成立。德日刑法通說均認為,行為人存在的諸如憎恨、激憤或者報復等其他動機可以與防衛(wèi)意思并存,不影響正當防衛(wèi)的成立。[16]
可見,傳統(tǒng)“意圖中心論”對互毆的定義并無規(guī)范質(zhì)量,通過主觀上的傷害故意、侵害故意、斗毆意圖、報復動機等來區(qū)分互毆與防衛(wèi)是徒勞的。
(二)互毆的實質(zhì)限縮解釋——真正的互毆與不真正的互毆
互毆既非法律術語,也非規(guī)范的教義學概念,互毆規(guī)范含義及其限縮解釋路徑的尋找必須回歸到正當防衛(wèi)的本質(zhì)原理上來。正當防衛(wèi)的原理,一直是結(jié)果無價值論和行為無價值論爭論的核心領域。是堅定的結(jié)果無價值論者,堅持法益衡量的優(yōu)越利益說。[17]詳細展開這一立場,不是本文的任務,這里只能簡要闡述。德國的個人權(quán)利保護說與我國刑法第20條規(guī)定的“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不符。德國的法秩序確認說的核心思想就是法規(guī)范效力的維護,可是無論是法規(guī)范還是法秩序,其背后依然是利益,因為“規(guī)范在這里只是達到維護法益這一目的的工具”。[18]德國通說將個人權(quán)利保護說與法秩序確認說合并形成的二元論也無法避免上述弊端。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犯罪的本質(zhì)是侵害法益,正當防衛(wèi)是緊急情況下法益沖突的風險分配機制。將正當防衛(wèi)阻卻違法的原理奠定在法益衡量的基礎上,與刑法保護法益的基本原理是相吻合的。互毆跟其他不符合正當防衛(wèi)的情形一樣,其不成立正當防衛(wèi)的根本依據(jù)是不存在需要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需要特別聲明的是,這里優(yōu)越利益判斷是質(zhì)的優(yōu)越性,而不是單純地量的計算。任何不符合正當防衛(wèi)的行為都是因為不符合優(yōu)越利益原理,這一點并不因為互毆而所有不同。互毆雙方是“不正對不正”,不存在需要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從根本上不符合正當防衛(wèi)的本質(zhì)要求。
從這一基本原理出發(fā),對互毆的內(nèi)涵進行實質(zhì)限制解釋,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什么樣的互毆行為才會導致不存在需要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
,
只有在雙方事先約定相互攻擊的場合(簡稱約架),才導致不存在需要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從而排斥防衛(wèi)的成立,這是真正的互毆。
如果沒有約架,一方對另一方侵害,就有防衛(wèi)的余地。這里的約架具有主體的雙向性和內(nèi)容的相對確定性,主體的雙向性即是雙方相互約定而不包括單方斗毆;內(nèi)容的相對確定性即約定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進行相互攻擊。除約架外,傳統(tǒng)理論所討論的互毆現(xiàn)象,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互毆,與防衛(wèi)不是互斥關系,是否正當防衛(wèi)需要具體分析(下文詳述)。
這樣,借鑒刑法學中的不作為犯和身份犯的分類,將互毆類型化為真正的互毆(也可以說是狹義的互毆)和不真正的互毆
◎真正的互毆(純正的互毆)→約架(雙方事先約定相互攻擊)
◎不真正的互毆(不純正的互毆)→一般的故意傷害、防衛(wèi)意圖、預期侵害、自招侵害等。
闡述如下:
首先,雙方事先約定相互攻擊,即約架,就表明雙方都同意通過私下決斗的方式解決爭端,雙方實際上都放棄了法律對各自的保護。換言之,約架就表明各自承諾對方毆打己方,這類似于被害人承諾,不存在需要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19]屬于雙方自我答責。
其次,既然是約架,雙方都是不法侵害,雙方都知道將進行相互攻擊,缺乏緊迫性(正在進行不法侵害),并不存在國家來不及救濟的緊急情況;也缺乏“正對不正”的前提,是典型的“不正對不正”。因約架在先,所以互毆過程中,即使在某個爭斗的瞬間,表面上看一方在防御,另一方在進攻,呈現(xiàn)出正當防衛(wèi)的表象,但因約架在先,就會得出并不存在需要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的結(jié)論,因此并無正當防衛(wèi)的余地。在真正的互毆中,動手先后,并無實質(zhì)意義,因為在事先約定相互攻擊的情形下,“下手先后,只是出于權(quán)宜考慮,實際上雙方互為攻擊與防御的對象,而無所謂針對他方違法侵害實施正當防衛(wèi)的問題。”[20]
再次,約架將互毆認定的時點前置,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與“事先斗毆意圖”相比,約架顯然更具可操作性。約架本身就是一種行為,系斗毆實行之前的邀約行為。換言之,將互毆行為性質(zhì)認定的關鍵時點前置到相互攻擊行為之前的約定行為。這樣的約定行為具有實體的內(nèi)容,即雙方通過當面對話、電話、互聯(lián)網(wǎng)、書信、捎話等方式約定在某個時間、地點進行相互攻擊,具有客觀性,而不像意圖那樣潛藏于內(nèi)心,“摸不著看不見”。傳統(tǒng)觀點立足于斗毆行為開始后的“客觀上連續(xù)相互攻擊”無法解決互毆的泛化問題。因為正當防衛(wèi)在客觀上表現(xiàn)為一方不法侵害,另一方進行反擊,而且一般情況下不可能“一招制敵”讓不法侵害戛然而止,或者讓侵害人立即“束手就擒”,而是呈現(xiàn)多個“回合”的“連續(xù)相互攻擊”。如果將互毆界定為連續(xù)的相互攻擊,其結(jié)果會導致“還手就是互毆”“打架就是互毆”。”前述案例1羅某故意傷害案,按照判決的邏輯,劉某先持木棍毆打羅某,羅某出拳反擊,雙方就是互毆。但這樣的判決是難以接受的。幾乎所有的故意傷害、正當防衛(wèi)都可以表現(xiàn)為“連續(xù)相互攻擊”。但是“連續(xù)相互攻擊”未必都經(jīng)過約架,經(jīng)過約架的相互攻擊就成為互毆了。前述陳興良教授所引用的姜方平故意傷害案,因雙方并沒有約架的行為,根本就不是互毆。[21]姜方平與鄭永良此前就有矛盾,案發(fā)當天鄭永良先向姜方平父親挑釁,作為兒子的姜方平(此時并沒有準備工具)找鄭永良評理或要個說法尚在情理之中。在沒找到鄭永良后返回途中反被對方持鐵棍追打,且鄭永良先動手打姜方平。[22]這其實就是糾紛引發(fā)的故意傷害案件,不能輕易認定為互毆而否定正當防衛(wèi)。不能認為事先有糾紛、有矛盾、準備工具就一定是互毆。任何故意傷害案件都是有矛盾和糾紛的,沒有無緣無故的故意傷害,有的是偶發(fā)矛盾,有的長期矛盾,有的是新仇,有的是舊恨,不能一概認定為互毆而排斥正當防衛(wèi)。只有通過約架這個攔砂壩、擋土墻才能把互毆限定在合理的范圍之內(nèi)。
最后,傳統(tǒng)通說關于互毆中兩種正當防衛(wèi)的例外情況也需要重新審視。(1)約架的一方停止侵害(逃跑、求饒等)而另一方繼續(xù)侵害。停止侵害的一方實際上已經(jīng)放棄了約架和斗毆的行為,作為雙向行為的互毆,此時已經(jīng)結(jié)束。對方繼續(xù)侵害、追打,對于停止侵害的一方來說,屬于新的不法侵害,這時停止侵害一方的利益就取得了優(yōu)越地位,法律不能“見死不救”,停止侵害的一方具有正當防衛(wèi)的余地。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不是例外情況,而是產(chǎn)生了新的不法侵害。(2)輕微互毆中一方突然使用殺傷力很強工具。,在真正的互毆中,此種情況不存在正當防衛(wèi)的余地。既然是雙方約架,雙方都能預見到對方可能使用兇器,均在其概括預見的范圍之內(nèi),這不值得法律保護。傳統(tǒng)觀點之所以會認為這種情況下成立正當防衛(wèi),根本原因還是沒有區(qū)分互毆與一般的故意傷害。在一般的故意傷害案中,先動手的一方原則上不得主張正當防衛(wèi),但是在后動手一方突然使用殺傷力很強的器具時,先動手一方可以正當防衛(wèi)。但這根本不屬于真正的互毆,傳統(tǒng)觀點其實是將這種一般故意傷害案件當成互毆來處理,所以才會作為例外情形。因此可見,這種例外是不嚴謹?shù)模蛟S正是因為此,高銘暄和馬克昌教授分別在《刑法專論》和《犯罪通論》中論述互毆中正當防衛(wèi)例外情形時,僅列舉前述第一種情形,而對第二種情形只字未提。[23]
總之,互毆的概念應當從正當防衛(wèi)的基本原理進行實質(zhì)的限縮解釋,將互毆限定為事先約定相互攻擊(約架),才能將互毆與一般故意傷害案件區(qū)分開來。也許有人會說,這樣限制解釋會不會導致互毆的范圍過窄,進而出現(xiàn)防衛(wèi)權(quán)的濫用。,這樣的擔憂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限縮互毆的范圍,未必等于擴大防衛(wèi)的范圍,只是通過限縮解釋讓真正的互毆內(nèi)涵和界限更加清晰,認定更具可操作性。其他的不真正的互毆要么屬于一般的故意傷害,要么屬于防衛(wèi)意思、預期侵害、挑撥防衛(wèi),是否存在正當防衛(wèi)不能一概而論。
三、互毆中防衛(wèi)類型化之實體規(guī)則
(一)真正的互毆之認定規(guī)則
當我們把真正的互毆嚴格限定在約架范圍之內(nèi)的時候,其認定標準就清晰了。真正的互毆沒有正當防衛(wèi)的余地,即使是一方逃跑等也不屬于真正互毆的例外,而是互毆結(jié)束后產(chǎn)生新的不法侵害事實。真正的互毆主要包括以下類型:
(1)單挑型約架與群毆型約架。單挑型約架即單人之間事先約定相互攻擊,不存在正當防衛(wèi),根據(jù)具體案情定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群毆型約架,即二人或三人以上事先約定相互攻擊,不存在正當防衛(wèi),根據(jù)案情認定共同故意傷害、聚眾斗毆。
(2)復仇型約架與偶發(fā)矛盾型約架。前者是雙方原本就存在矛盾和仇恨,雙方約架,不存在正當防衛(wèi);后者是因偶發(fā)矛盾發(fā)生口角后,雙方約定再次通過打架解決,不存在正當防衛(wèi)。如果是偶發(fā)矛盾當時就引發(fā)雙方打架,并不存在約架,那就屬于一般的故意傷害案件,不屬于真正的互毆,有正當防衛(wèi)的余地。
(3)二次斗毆型約架。是指雙方發(fā)生第一次毆打后,雙方約定再次互毆,該情形下不存在正當防衛(wèi)。
(4)爭奪勢力范圍型約架。這類案件通常發(fā)生在團伙、黑惡勢力之間,通過約定互毆的方式爭奪勢力范圍。這些均屬于真正的互毆,不存在正當防衛(wèi)。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單方約架不屬于真正的互毆。如果一方以為是和解、談判等具有趕赴現(xiàn)場的合理理由,另一方借機毆打,屬于單方約架,不屬于真正的互毆,沒有約架的一方具有防衛(wèi)權(quán);或者一方為了約架而故意隱瞞,將另一方騙至某個地方進行毆打,也屬于單方約架,沒有約架的一方具有防衛(wèi)權(quán),不能認為沒有約架的一方只要還手就是互毆。單方約架的一方屬于不法侵害,沒有約架一方的利益處于優(yōu)越地位,因此可以正當防衛(wèi)。單方約架的一方原則上沒有防衛(wèi)權(quán),因為在其進行單方約架時就已經(jīng)放棄了法律對自己的保護,不具有優(yōu)越利益,只有在逃跑、求饒等放棄單方約架,形成新的不法侵害事實的情況下,才有正當防衛(wèi)的余地。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性案例(檢例第48號)正確地指出“單方聚眾斗毆的,屬于不法侵害,沒有斗毆故意的一方可以進行正當防衛(wèi)”。
(二)不真正的互毆之認定規(guī)則
不真正的互毆,情形極其復雜,有的屬于一般故意傷害,有的屬于預期侵害、有的屬于挑撥防衛(wèi)等,既可能存在正當防衛(wèi),也可能沒有正當防衛(wèi)的余地,有必要進行類型化的研究。
1.一般故意傷害案中正當防衛(wèi)的認定規(guī)則。在因民間糾紛、生活瑣事、口角爭吵等引發(fā)的打架,只要沒有約架,就屬于一般的故意傷害案件,不能絕對排除正當防衛(wèi)的余地。這類案件應當盡可能分清起因的是非對錯和動手先后順序。如果一方先尋釁滋事或者先動手,另一方的正當防衛(wèi)余地更大,先動手的一方一般不能主張正當防衛(wèi)。其法理依據(jù)在于,先動手一方制造了不法侵害,利益保護的優(yōu)越性明顯降低,“最先發(fā)動攻擊者必須容忍對方的防衛(wèi)”。[24]例如前述案例2熊某某故意傷害案,對方酒后無故滋事、動手在先,熊某某可以正當防衛(wèi)。
當然,也并非先動手一方絕對不能正當防衛(wèi)。如果先動手一方只是輕微毆打,后動手一方使用致命性暴力襲擊;或者是后動手一方突然使用殺傷力很強的武器;或者先動手一方已經(jīng)逃跑、求饒,此時先動手一方并非不能防衛(wèi)。前述案例4李某故意傷害案,盡管李某先動手,但是在逃跑被追打及圍毆過程中,依然具有防衛(wèi)權(quán)。因為先動手者逃跑后,由其先前制造的不法侵害已經(jīng)結(jié)束,對方的追擊行為形成一個新的不法侵害,此時被追擊者的利益處于優(yōu)越地位,可以防衛(wèi)。
綜上,糾紛、矛盾、口角引發(fā)的傷害案件中正當防衛(wèi)的認定規(guī)則可以概括為:
(1)一般故意傷害案中,要破除“打架就是互毆”的慣性思維,注意查明是非對錯和誰先動手,在雙方力量沒有較大懸殊,“武器對等”的情況下,原則上后動手一方可以進行防衛(wèi),先動手一方不能主張防衛(wèi);
(2)特定情況下,如先動手一方只是輕微毆打,后動手一方使用致命性暴力襲擊;或者是后動手一方突然使用殺傷力很強的武器;或者先動手一方已經(jīng)逃跑、求饒,此時先動手一方存在防衛(wèi)的余地。
2.防衛(wèi)意思與報復等動機并存案件中正當防衛(wèi)的認定規(guī)則。正當防衛(wèi)的成立是否需要防衛(wèi)意思,是行為無價值論和結(jié)果無價值論爭論的焦點。我國傳統(tǒng)通說主張防衛(wèi)意思必要說,并且認為同時具備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前者是對防衛(wèi)事實的認識,后者是對防衛(wèi)行為之目的、動機等,而且更側(cè)重于意志因素,所以通說習慣于將正當防衛(wèi)的主觀條件表述為“防衛(wèi)意圖”而不是“防衛(wèi)意思”。[25]“意圖”就是“圖…的意思”,就是“希望達成…目的的意思”,其實就是“動機”或“目的”。[26]這種誤用也顯示出通說對目的和動機等意志因素的側(cè)重。這就導致司法實踐中只要有報復、激憤或其他不道德動機,就會認定為互毆進而否定防衛(wèi),要求防衛(wèi)意圖與攻擊、報復等動機不能并存。這種“道德潔癖”[27]與傳統(tǒng)通說對防衛(wèi)意圖的重視密切相關。
在正當防衛(wèi)的認定,特別是涉及互毆問題時,應當?shù)酥寥∠饔^要素,特別是目的、動機等主觀要素。
首先,正當防衛(wèi)在犯罪構(gòu)成中屬于違法性階層的判斷,根據(jù)從客觀到主觀的犯罪認定思路,目的和動機等主觀要素,原則上應該在有責性中判斷。違法性評價并不取決于行為人的動機。[28]是否存在緊迫的不法侵害、是否存在需要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是正當防衛(wèi)成立的關鍵,而這些關鍵要素的判斷取決于客觀情狀,而不是內(nèi)在動機和目的。
其次,正當防衛(wèi)本質(zhì)上系緊急情況下的自救權(quán),是防衛(wèi)人做出的瞬間反應。在這種緊急狀況下,行為人冷靜地在大腦中產(chǎn)生正當防衛(wèi)的目的和動機,實屬罕見。倘若嚴格要求行為人對緊急情況下所實行之行為必須具有明確之目的、動機,必將導致大量的正當防衛(wèi)案件無法成立。
再次,在正當防衛(wèi)中,一般人面對不法侵害,都會產(chǎn)生憤怒、報復等動機,苛求防衛(wèi)人完全與這些“不道德”動機隔絕,是不現(xiàn)實的。也正因如此,當今日本的學說和判例均認為防衛(wèi)意思與攻擊意思(積極加害意思)并存時,并不影響防衛(wèi)的成立,“防衛(wèi)意思之內(nèi)容較以往判例更加稀薄化,故與其將防衛(wèi)意思視為防衛(wèi)之意圖或動機,不如說是接近防衛(wèi)之意識,此乃反映著將積極加害意思從防衛(wèi)意思之問題移至急迫性之問題”。[29]至于我國刑法第20條規(guī)定的“為了……”完全可以解釋為防衛(wèi)的起因條件,即防衛(wèi)行為必須是針對不法侵害。與德國刑法一樣,這里的“為了……”聽起來似乎是主觀性的表達方式,實際上表達的是一種客觀的防衛(wèi)性行為,[30]至多只需要行為人認識到對方是在進行不法侵害的客觀事實即可。
最后,從德日刑法發(fā)展脈絡看,防衛(wèi)意思經(jīng)歷了從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同時具備,走向防衛(wèi)意志因素的剔除,再到防衛(wèi)意思的淡化和純化的過程。[31]日本刑法學界曾經(jīng)認為防衛(wèi)意思要同時具備防衛(wèi)認識和防衛(wèi)目的,但是1970年以后的理論界和實務界逐步認識到,嚴格要求防衛(wèi)意思須兼具防衛(wèi)之意圖或動機,會不當限縮正當防衛(wèi)之成立范圍,從而就出現(xiàn)了將防衛(wèi)意思內(nèi)容單純化的趨勢。現(xiàn)在日本通說認為采防衛(wèi)意思僅須認識正當防衛(wèi)的事實,而不要求同時具備防衛(wèi)目的和動機。這樣,實際上已架空了防衛(wèi)的意志因素,“此種要素在判例與通說之觀點上,早已僅是用語之要求而已”。[32]德國通說也認為防衛(wèi)意思只要對正當防衛(wèi)情形有認識,有意識地對攻擊進行抵抗即可,不要求具有防衛(wèi)目的和意圖。[33]防衛(wèi)意圖在正當防衛(wèi)成立條件中的作用越來越有限。我國刑法學不能不顧這種發(fā)展趨勢而固守已過時的防衛(wèi)認識與防衛(wèi)意志同時具備的學說。
綜上,防衛(wèi)意思與報復等動機并存時的正當防衛(wèi)認定規(guī)則可概括為:
(1)原則上不需要考慮防衛(wèi)意思,即使要考慮防衛(wèi)意思也僅能限于認識因素,并盡可能地純化,行為人至多只需要認識到不法侵害的事實。
(2)只要客觀上符合正當防衛(wèi)的條件,即使是出于憤怒、報復等動機,也是可以被正當化的。[34]
(3)防衛(wèi)人主觀具有傷害意圖、積極加害意思,并不影響正當防衛(wèi)的認定。“一個人在適當?shù)木o急幫助中傷害了一名攻擊者,他的行為就是合法的,即使對他來說,重要的并不是保護被害人,而是教訓一下攻擊者”,[35]依然成立正當防衛(wèi)。
(三)預期侵害中正當防衛(wèi)的認定規(guī)則
預期侵害是指行為人在事先已經(jīng)預知將受到不法侵害,而實施反擊。[36]我國司法實踐中一般會將預期侵害作為事先有傷害意圖、斗毆意圖而認定為互毆,進而否定正當防衛(wèi)。換言之,互毆概念的泛化導致預期侵害在實踐中幾乎沒有例外地被歸結(jié)為互毆,還動輒強加退避義務,導致正當防衛(wèi)與緊急避險的混同。前述案例5聶某某故意傷害案的判決書要求被告人在被多人持械追打時只能采取緊急避險,而不能正當防衛(wèi)。這種論調(diào)令人吃驚!
這種粗放式的處理方式值得反思。需要明確的是,預期侵害不是真正的互毆。既然不是真正的互毆,那就并非一概不成立正當防衛(wèi)。德日刑法學通說也認為預期侵害并非一律不成立正當防衛(wèi)。至于退避義務,一般認為,正當防衛(wèi)與緊急避險是不同的,正當防衛(wèi)基于“正不必向不正讓步”的信條,不能賦予被侵害人的退避義務。日本最高裁判所也否認預期侵害中的退避義務,但是同時又認為“預期侵害+積極加害意思”就否定正當防衛(wèi)。[37]而日本學界很多觀點認為預期侵害在特定條件下應該課予防衛(wèi)人退避義務。[38]
正當防衛(wèi)與緊急避險不同,除不法侵害來自于無責任能力人、親屬等密切關系人以及下文所述特定類型的挑撥防衛(wèi)外,原則上應當否定退避義務,預期侵害無需引入退避義務理論。
首先,退避義務與正當防衛(wèi)“正不必向不正讓步”的法理不符。德國通說認為正當防衛(wèi)一般不需要退避義務,只是在對于無責任能力人、親屬等具有保證關系、特定條件下的挑撥防衛(wèi)承認退避義務。[39]我國臺灣地區(qū)通說否定退避義務。[40]
其次,退避義務解決的是預期侵害在特定情況下不成立正當防衛(wèi)的問題,但是不成立正當防衛(wèi),完全可以通過不符合正當防衛(wèi)的條件以及其本質(zhì)原理來判斷,無需引入讓公民產(chǎn)生誤解的“退避義務”(僅在挑撥防衛(wèi)中具有意義,見下文)。預期侵害何時成立正當防衛(wèi),何時不成立當防衛(wèi),應當從優(yōu)越利益原理的角度進行實質(zhì)解釋,關鍵看有無需要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積極加害意思”理論也好,退避義務理論也罷,其實只不過是正當防衛(wèi)本質(zhì)原理的投影。預期侵害中的正當防衛(wèi)認定與否,不需要退避義務理論也完全能夠順利解決,具體類型如下:
(1)當行為人預期到侵害時,沒有合理的理由而徑直前往進行毆打,那就意味著行為人承諾放棄法律對自身利益的保護,屬于“不正對不正”,就沒有需要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這其實不是退避義務問題,而是類似于單方約架。
(2)當行為人預期到侵害時,具有合理的理由而前往,例如像日本學者橋爪隆所說的,前往現(xiàn)場是正當職務行為;又如在朋友遭受不法侵害且自己被侵害的危險性亦高;[41]再如,行為人前去談判、和解、賠禮道歉等,如果遭遇對方的不法攻擊,行為人的法益處于優(yōu)越地位,可以防衛(wèi),沒有退避義務。
(3)行為人預期到侵害,沒有合理理由在特定地點“守株待兔”,與對方較量,這與前面第一種情況一樣,承諾放棄法律對自身利益的保護,屬于“不正對不正”,沒有需要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這也不是退避義務問題,而是類似于單方約架。
(4)行為人預期到侵害,但是具有合理的理由而滯留一定場所,或者是前往某處的必經(jīng)之地,遭遇對方的不法侵害,可以進行防衛(wèi)。例如行為人在自己家里或者上班時間在辦公室,或?qū)Ψ剿诘牡攸c是行為人回家的必經(jīng)之地或者是接孩子放學的必經(jīng)之地,均不能因預期到侵害就否定正當防衛(wèi)。原因在于待在家里、辦公室,以及前往某處的行動自由屬于憲法性利益,屬于值得保護的優(yōu)越利益。不能因為行為人與對方發(fā)生口角后,預期到對方可能會來報復,而讓行為人搬家或者限制行動自由。否則,諸如“去想去的地方的自由”、“呆在自己家里的自由”這些正當利益就會受到侵害,而造成被侵害者需要屈服于侵害者、限制自己行動自由的結(jié)果,這就無異于變相承認“非法侵害”人的利益實際上要優(yōu)于被侵害者的利益。[42]
(5)預期到侵害時,為消極防御而準備工具,不影響正當防衛(wèi)的認定。行為人的優(yōu)越利益不會因為對不法侵害有所預期準備工具防身而喪失。例如,長期受高年級學生欺凌的行為人,預期放學路上會被對方毆打,而準備防身工具,在遭遇對方主動攻擊時進行反擊,屬于正當防衛(wèi)。
(四)自招侵害(挑撥防衛(wèi))中的正當防衛(wèi)認定規(guī)則
我國刑法理論對挑撥防衛(wèi)缺乏類型化的精致研究,通說認為挑撥防衛(wèi)人主觀上具有加害對方的目的而并無防衛(wèi)的意圖,因此不成立正當防衛(wèi)。[43]實踐中要么將挑撥防衛(wèi)直接作為互毆處理,要么認定為挑撥防衛(wèi)而排除正當防衛(wèi)的成立。比如下面這個案例:
【案例6毛某某故意傷害案】被告人毛某某與伍某因地界爭吵,伍某持磚頭打傷毛某某頭部(輕微傷),致毛某某倒地。毛某某受傷后大聲叫罵,伍某又沖向毛某某,毛某某撿起一塊磚頭打傷伍某左額頭(輕傷二級)。判決認為,毛某某被打后,在對方行為停止后,又以言語激怒對方,促使對方欲實施不法侵害,導致雙方在互毆中毛某某持磚頭致傷被害人,毛某某的行為屬挑撥防衛(wèi),不屬正當防衛(wèi)。[44]此案判決認為屬于互毆,同時又認為是挑撥防衛(wèi),因此不成立正當防衛(wèi)。這是值得商榷的。
如前所述,以防衛(wèi)意圖欠缺為由否定正當防衛(wèi)是不可取的,對挑撥防衛(wèi)不加區(qū)分地全盤否定防衛(wèi)是草率的。挑撥防衛(wèi)的認定規(guī)則,同樣要回到正當防衛(wèi)正當化原理上來。防衛(wèi)行為的本質(zhì)是優(yōu)越利益的衡量,也就是利益沖突的平衡,在挑撥防衛(wèi)中表現(xiàn)為利益風險分配。當我們要從規(guī)范角度來評價防衛(wèi)人所欲保護的利益是否處于優(yōu)越地位時,應該關注防衛(wèi)人所受侵害的利益與所保護的利益之間的權(quán)衡關系,當防衛(wèi)人的利益在一個利益沖突的狀況下具有優(yōu)先地位時,侵害人的利益就必須退讓;至于防衛(wèi)人的利益是否具有優(yōu)先地位的判斷,則是取決于侵害人對于這個激烈的沖突局面所應負責的程度或范圍。[45]換言之,正當防衛(wèi)其實就是一種利益沖突的平衡和風險分配的制度設計,而誰對這個沖突應負責任,誰的利益在規(guī)范評價上就不具有保護的優(yōu)越性,至少是優(yōu)越性減損,這樣的風險分配機制也符合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由于挑撥在先,其法益的優(yōu)越地位必然下降,從風險分配的角度來說,嚴格限制挑撥人的防衛(wèi)權(quán)是妥當?shù)摹H绾螄栏裣拗铺魮苋说姆佬l(wèi)權(quán)呢?就是讓其承擔一定的退避義務。這種退避義務,不是“正對不正的讓步”,也不是“正無需向不正讓步”的例外,而是基于風險分配的需要,由挑撥人對自己先行制造的風險自我容忍、自我答責,通過退避來回贖、抵消先前制造的風險,直到其利益重新恢復到優(yōu)越地位之后,才能正當防衛(wèi)。美國刑法中的“真誠退卻”義務的意義也在于切斷先前過錯行為與防衛(wèi)行為之間的聯(lián)系。[46]從類型化認定規(guī)則建構(gòu)的角度來說,可以借鑒德國刑法學的分類,將挑撥防衛(wèi)分為蓄意型挑撥和非蓄意型挑撥。[47]
1.蓄意型挑撥。蓄意挑撥是指挑撥人蓄意挑釁或者激怒被挑撥人,并利用被挑撥人因受刺激而向挑撥人發(fā)動攻擊的機會,借正當防衛(wèi)之名對被挑撥人進行攻擊。蓄意型挑撥原則上應該否定正當防衛(wèi),但是特定情況下有正當防衛(wèi)的余地。因為行為人蓄意制造利益沖突,從風險分配角度來說,其法益受保護的優(yōu)越性明顯降低,挑釁人不得借機防衛(wèi),具有退避義務。但是,在特定條件下,也不能排除防衛(wèi)的可能性。具體來說:
(1)挑釁行為本身較為輕微,與對方的攻擊行為相比,明顯不成比例;
(2)在具備退避條件時已經(jīng)退避,但已退無可退。在這種情況下,挑撥人的利益就恢復到優(yōu)越地位,可以正當防衛(wèi)。案例6中,毛某某被對方毆打后大聲叫罵有可以理解之處,是否屬于蓄意挑撥尚且難以證明,即使屬于蓄意挑撥,這種挑撥行為本身較為輕微,在對方再次沖上來毆打時,倒在地上的毛某某無法躲避,撿起磚頭反擊,當屬防衛(wèi)。
2.非蓄意型挑撥。非蓄意型挑撥是指于挑唆者并非有意借用正當防衛(wèi)來傷害對方并規(guī)避刑事責任,而是因言語或行動等其他可責難的方式引起對方的不法侵害。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傳統(tǒng)理論與司法實踐,大多將這些非蓄意型挑撥作為互毆而排除防衛(wèi)。其實,這些類型并不屬于真正的互毆,不得輕易否定防衛(wèi),應當按照挑撥防衛(wèi)的理論具體類型化分析。具體可以分為:
(1)過失的非蓄意型挑撥。例如,甲乘坐高鐵調(diào)整座椅,不小心(過失)導致后排乘客乙的小桌板上的水杯傾倒,乙脾氣暴躁立即出拳毆打甲,甲予以反擊,此時不能認定為真正的互毆,應當認為甲具有完整的防衛(wèi)權(quán)。至多有些情況下“因自己的行為招致了侵害,防衛(wèi)行為欠缺相當性,從而成立防衛(wèi)過當”。[48]
(2)故意的非蓄意型挑撥系違法行為(包括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民事法行為)。因為行為人制造了不法侵害,其利益的優(yōu)越性會降低,其防衛(wèi)權(quán)應當按照“防衛(wèi)三階段”進行限制,即躲避——防御防衛(wèi)——攻擊防衛(wèi),也就是受攻擊者必須先行躲避;如果行不通,則必須在人們可期待他實施防御性行動的時候,實施防御性行動;再不行,才可以采取攻擊防衛(wèi)。[49]
(3)故意的非蓄意型挑撥系合法僅違反倫理的,或者系合法且合倫理的,原則上具有完整的防衛(wèi)權(quán)。僅違反倫理甚至連倫理都沒有違反的情況下,挑撥人沒有制造不法侵害,沒有理由讓挑撥人承擔不利的風險分配,不具有退避義務。例如,我國臺灣學者許恒達舉例:債權(quán)人甲告訴債務人乙(情緒不佳、可能打人且眾人皆知),若不于明日返還欠款,將向法院起訴,乙即刻大怒,隨即出拳作勢打甲,甲拿起身邊手提袋擲向乙,造成乙受輕傷。[50]甲索要債務合理合法,具有完整的防衛(wèi)權(quán)。
四、互毆中防衛(wèi)類型化之程序規(guī)則
真實案例或者具體法律爭端的解決,從來都是實體與程序的交錯使用,[51]對于互毆與防衛(wèi)來說更是如此。限于篇幅下面主要圍繞證明對象展開。[52]
(一)真正的互毆之證據(jù)規(guī)則
關于互毆的傳統(tǒng)理論與實踐,在證據(jù)上存在以下弊端:(1)立足于“意圖中心論”界定互毆,但“意圖”幾乎無法證明。“事先斗毆意圖”“報復動機”“侵害意圖”潛藏于行為人內(nèi)心,在證明對象的分類上屬于內(nèi)部事實。內(nèi)部事實又稱內(nèi)心事實,其證明具有消極性、浮動性、抽象性,證明方法較為狹隘。[53]“意圖中心論”導致的程序性后果就是“口供中心主義”盛行。因為有無某種意圖和動機,被告人的口供是最直接的證據(jù)。實體刑法要求犯罪要有內(nèi)在的或主觀的要素(預謀、動機),那么,被告人供述的內(nèi)部事實是唯一的直接證據(jù)。[54](2)長期以來,司法實踐對于互毆案件的證明對象側(cè)重于相互攻擊開始之后的事實,忽視相互攻擊開始之前約架行為的證據(jù)收集和審查。這與實踐“不分是非對錯”的現(xiàn)象是一體兩面的關系。
按照提出的將真正的互毆限定為事先約定相互攻擊(約架),能夠避免上述證明困境。
首先,將互毆界定為約架,走出“意圖中心論”,使證明對象客觀化。與“事先斗毆意圖”“侵害意圖”“報復動機”等相比,約架更具可操作性。約架是一種行為,在證明對象上屬于外部事實,“其證明較具積極性,實體性與具體性”。[55]約架具有實體的內(nèi)容,即雙方通過當面對話、電話、互聯(lián)網(wǎng)、書信、捎話等方式約定在某個時間、地點進行相互攻擊,這些都會留下證據(jù)。
其次,將互毆界定為約架,實現(xiàn)了證明對象的前置化,也就是從以往側(cè)重于證明相互攻擊開始后的證據(jù),轉(zhuǎn)變?yōu)榧纫⒅叵嗷ス羰聦嵉淖C明,也注重相互攻擊開始之前約架事實的證明,從而倒逼偵查及司法機關改變“不分是非對錯”的習慣做法。
(二)不真正的互毆之證據(jù)規(guī)則
1.一般故意傷害案件中正當防衛(wèi)的證據(jù)規(guī)則。在一般故意傷害案中,誰先動手對防衛(wèi)的認定具有重要意義。要改變動輒以“瑣事”“互毆”的表述代替是非對錯和動手先后的精細化認定。“需要嚴格加以考察的是,誰先動了手。因為先遭到攻擊的人,可以自衛(wèi)”,[56]實踐中要盡可能收集和審查誰先動手的證據(jù)。
實踐中大量案件從證據(jù)上無法分清誰先動手,這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在于一些傷害案件瞬間發(fā)生或者發(fā)生在“一對一”的封閉空間,沒有視頻監(jiān)控等其他證據(jù)的情況下,難以判斷誰先動手;主觀原因在于偵查人員、司法人員基于“打架就是互毆”“不分是非對錯”的慣性思維。對于因客觀原因無法查清動手先后的情況下,應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則處理。即便查不清動手先后順序,這樣的認定規(guī)則也具有一般預防意義,既可以實現(xiàn)倡導不首先使用暴力的消極一般預防,也可以形成遵守規(guī)則的積極一般預防,也符合正當防衛(wèi)本身在立法上“追求一種一般預防目的”。[57]
2.防衛(wèi)意思與報復動機并存案件中正當防衛(wèi)的證據(jù)規(guī)則。如前所述,我國傳統(tǒng)理論認為防衛(wèi)意思要同時具備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且更側(cè)重意志因素,這種“重欲輕知”的傾向不僅在實體法上容易滑向主觀主義刑法的泥潭,在程序法上也面臨證明困境的責難。事實上,防衛(wèi)人的利益處于優(yōu)越地位與防衛(wèi)人心里是怎么想的無關,更何況防衛(wèi)人的動機和目的在證據(jù)上難以證明。正如羅克辛所言,要求正當防衛(wèi)具備防衛(wèi)的意志因素毫無意義,因為“在實踐中從來都是不能證明的”。[58]如前所述,德日刑法在防衛(wèi)意思問題上經(jīng)歷了從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同時具備,走向意志因素的剔除,再到認識因素的淡化和純化的過程。普遍的共識是防衛(wèi)意思和攻擊意思并存的場合,具有評價為正當防衛(wèi)的余地。[59]這一變化在證據(jù)法上的意義在于證明對象的客觀化。正當防衛(wèi)的認定,特別是涉及互毆問題時,應當?shù)酥辽釛墝δ康摹訖C等主觀要素的考量。即便采用防衛(wèi)意思必要說,證明對象也僅限于認識因素,即至多只需要證明行為人對防衛(wèi)事實有認識即可。
3.預期侵害中正當防衛(wèi)的證據(jù)規(guī)則。日本判例發(fā)展出的“預期侵害+積極加害意思”理論不值得借鑒,除了前述實體法理由之外,在證據(jù)法上也有重要理由。“積極加害意思”與目的、動機等主觀超過要素一樣難以證明。預期侵害的證據(jù)規(guī)則在于:
(1)證明對象的前置化,注意收集和審查證明事情起因的證據(jù),也就是要證明行為人對即將到來的不法侵害是否有預期,不能盲目地認定為互毆而排斥防衛(wèi)。
(2)要注意證明行為人前往現(xiàn)場、滯留于一定的場所、消極準備防御工具等行為是否具備合理的理由。
4.自招侵害(防衛(wèi)挑撥)中正當防衛(wèi)的證據(jù)規(guī)則。傳統(tǒng)“意圖中心論”從缺乏防衛(wèi)意圖的角度來論證挑撥防衛(wèi)不成立正當防衛(wèi),除了面臨實體刑法上的責難,也面臨證據(jù)法上的困境。正如羅克辛所言,“在實踐中,這種有目的的挑釁從來沒有出現(xiàn),或者至少出現(xiàn)是無法證明的”。[60]對于蓄意型挑撥而言,證明更加困難,要求行為人必須事先經(jīng)過周密策劃,形成了“引蛇出洞繼而借助正當防衛(wèi)之名侵害對方的想法。但是,除非被告人或者同謀者自行招供,否則行為人究竟是否具有內(nèi)容如此明確的意圖,實際上是極難查清的。”[61]因此,典型的蓄意型挑撥真實案例幾乎不可能出現(xiàn),實踐意義有限,重點是非蓄意型挑撥。非蓄意型挑撥證明對象也要前置到挑撥行為上,重點收集和審查以下證據(jù):
(1)挑撥前行為是故意還是過失,是違法還是合法,是違反倫理道德還是情有可原、人之常情;
(2)行為人有無退避,退避的可能性、現(xiàn)實性、可行性如何。
總之,與實體法上互毆的類型化相對應,其證明對象應當客觀化和前置化,這樣更易于證明,也更具可操作性。
結(jié)語
傳統(tǒng)理論關于互毆概念的泛化及其與防衛(wèi)互斥關系的簡單化,是導致故意傷害案件中認定正當防衛(wèi)呈“萬里挑一”現(xiàn)象的根本原因,也是正當防衛(wèi)刑法條文“僵尸化”的重要原因。在互毆與防衛(wèi)問題上,必須在互毆之外看互毆,在優(yōu)越利益基本原理之上看互毆,在實體與程序之間看互毆,在將互毆分為真正的互毆與不真正的互毆的基礎上進一步類型化。根據(jù)本文的觀點來重新考察第一部分各種類型的實踐亂象:
◆打架未必是真正的互毆;
◆還手完全可能是正當防衛(wèi);
◆有傷害意圖或報復動機并不能否定正當防衛(wèi);
◆事先有糾紛或準備工具只是表明有預期侵害,并非一概不能防衛(wèi);
◆先動手者并非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防衛(wèi);
◆防衛(wèi)原則上無需先行躲避,即防衛(wèi)人原則上不具有退避義務。
既不能以“誰死傷誰有理”進行武斷化處理,也不能以泛化的互毆進行簡單化處理,而應當實質(zhì)、具體地分析其是真正的互毆還是不真正的互毆。如果是真正的互毆則否定防衛(wèi),如果是不真正的互毆,則應回歸到一般的故意傷害、防衛(wèi)意圖、預期侵害、自招侵害等框架下,結(jié)合實體和證據(jù)的類型化認定規(guī)則進行具體分析和認定。